律师按语:“不因犯罪而获益”的法谚是刑法发挥一般预防作用的功利主义原理。在贿赂案件中,全面、彻底地消除行为人的获益,是司法机关打击和预防此类案件的重要手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行贿所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依法予以没收,不正当非财产性利益要予以纠正。在追缴制度的实践中,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所得范围的划定仍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司法判决对于追缴的适用范围也有所区别。尤其是在单位行贿罪案件中,行为人往往并不直接获得财产性利益,而是通过行贿获取不正当机会,以合法行为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定收益系“因”犯罪行为而获得,从而认定为违法所得,进而确定违法所得的追缴范围,理论和实践上往往存在较大争议。笔者尝试结合学术理论、司法判例和刑事政策对单位行贿案件中违法所得的追缴范围进行分析,以期对司法实务起到助益,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一、我国刑法关于追缴的规定及其制度内涵
(一)我国刑法中关于追缴制度的规定
当前我国追缴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即《刑法》第64条规定的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和《刑法》第53条规定的对未足额缴纳罚金的追缴,特别性的规定是《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的对于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以非法所得论,予以追缴。其中,《刑法》第53条的规定是对于刑罚的确认和补充,《刑法》第64条和第395条则是一般意义上对追缴的规定。此外,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了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依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责令退赔或者返还被害人。因行贿犯罪取得财产性利益以外的经营资格、资质或者职务晋升等其他不正当利益,建议有关部门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二)我国追缴制度的规范内涵
对于我国追缴制度规范内涵的把握是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关键。首先,应明确在相同的意义上理解《刑法》第64条中的违法所得和行贿罪规定中的“不正当利益”中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从文义的角度“不正当财产性利益”的范围要大于违法所得,但不正当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不应超过依据《刑法》第64条、第395条划定的不法性的范畴,《刑法》第64条的规定包含了没收违法所得和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法律后果,而《刑法》第395条“以非法所得论,予以追缴”的规定,说明其是通过法律拟制将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拟制为非法,前者是将与违法行为直接相关的财产予以追缴,后者是将没有合法根据的财产予以追缴。进一步概括而言,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追缴规定的制度目的的核心在于追缴财产的不法性,这种不法性是违法相关与无合法来源的总和。
二、违法所得的范围厘清
(一)违法所得范围的理论分析
首先,根据违法所得是否直接通过违法行为获得,分为直接违法所得与间接违法所得。其次,将间接违法所得——也就是通过直接违法所得获取的收益——分为直接违法所得的孳息和投资收益。[1]对于直接违法所得及其孳息应予追缴,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理论学说中均无争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4条规定应对财物及其孳息依法做出处理。关键争议在于对直接违法所得投资形成的收益是否应予追缴,基于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提前得出结论,对于投资收益是否应予追缴,需围绕不法性为核心进行实质判断。
早期理论对于投资收益追缴的态度呈现两极化趋势,或者认为投资收益是基于在先的不法所得,应当全部予以追缴,或者认为应切割不法所得与后续合法经营之间的关系,对合法经营所得不予追缴。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均对投资收益的部分特征进行确认,但都有片面之嫌。在实践中会形成投资收益的判断难题,恰恰是因为其中同时具有不法与合法要素,不法要素与合法要素同时作用于收益的取得,对此有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来判断在投资收益中合法性因素与违法性因素的主导性[2]。此外也不应忽视刑事政策的影响,在不同的罪名中进行不同的实质判断。
具体而言可以遵循如下判断规则。其一,投资收益取得的主导因素。其二,基于刑事政策作宏观把握。由于在先的违法性,这一判断路径的核心实际上是合法性因素的介入及其作用大小。如果合法因素和不法因素可以进行区分,例如均为资金投资,则按照比例进行追缴。如果合法因素和不法因素不能进行区分,则一般地基于合法因素和不法因素的主导性进行判断,同时特别地基于刑事政策作不同的态度倾斜。例如对于一般民营企业的经济犯罪,当合法要素和不法要素不分主次发生作用时,可以原则上不予追缴。对于行贿罪则可以原则上予以追缴。
(二)违法所得范围的实践判例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违法所得追缴的范围,学理上的讨论也并不深入,因此实践中司法机关做出的判决就成为主要的参考依据。
在权威案例中,《刑事审判参考》第787号、第1282号案例判决书中均未提及追缴违法所得。在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的五起行贿犯罪典型案例中,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江西王某某行贿案和四川刘某富行贿、非法采矿案的判决书中均载明追缴违法所得。其中,江西王某某行贿案中,行为人行贿是为了本公司在被收购时获得高价,办案机关对转让的公司股份价格进行了司法鉴定,将总收购价除去收购时行贿人公司实际价值,认定违法所得的范围并判决予以追缴。而在另两件案件的判决中,均载明了对被告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未明确追缴的违法所得的具体范围。
笔者进一步浏览了威科先行数据库中近年来的400多起单位行贿罪案例,可以根据这些裁判文书对于追缴违法所得适用的态度将其归纳为五类:(1)未载明追缴违法所得的;(2)追缴的违法所得是受贿人退还给行贿人的款项的;(3)追缴的违法所得是行贿人主动退缴的款项的;(4)载明追缴违法所得,但未明确违法所得的范围的;(5)载明追缴违法所得,并明确违法所得的范围的。
在笔者整理的裁判文书中,绝大多数都未载明追缴违法所得。此类裁判文书中行贿人的行贿目的通常是取得竞争优势、在日常经营中获得帮助等难以通过数额计算的不正当利益,但也有部分案件中行贿人的行贿目的是获取项目、获取地块等可以计算数额的不正当利益。因此可以得出的第一点结论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追缴违法所得的判决较少。原因可能一方面基于所涉案件中违法所得难以量化,另一方面也与司法机关对于判决中是否载明追缴违法所得的模糊态度有关。
在载明追缴违法所得的裁判文书中,部分文书将受贿人退还给行贿人的款项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另有部分文书以行贿人退缴的款项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也有文书仅提及行贿人退缴款项,并未申明予以追缴。其中,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做出的新余市创晟商贸有限公司、吴维民单位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在说理部分指出了可能的原因:由于单位行贿罪案件中违法所得计算较为复杂,尤其是在案件中仅有被告人供述作为确定违法所得范围的证据时,部分法院倾向于依照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按照被告在案中主动退赃的金额认定违法所得。
还有部分裁判文书采取了同行贿罪经典案例文书中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和四川刘某富行贿、非法采矿案一样的策略,即在判决中载明追缴违法所得,但并未实际划定违法所得的范围。由此可见部分法院仅在判决中将追缴违法所得作为宣告性的措施。
笔者将上述裁判文书中第(5)类可供有效参考的案例按照“行贿目的+追缴违法所得判决原文”的方式总结为表格,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类型化分析。
1.裁判文书整理归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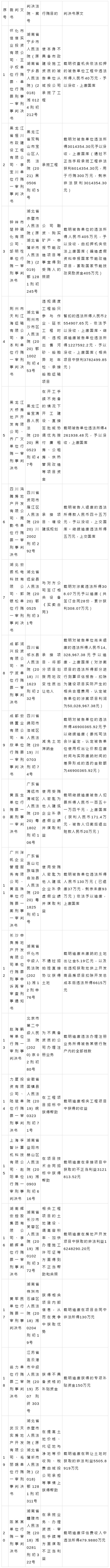
2. 违法所得的类型化分析
笔者将上述可供有效参考的案例根据行贿人行贿目的不同,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项目型”;(2)“差价型”;(3)“资质型”。
“项目型”案件是单位行贿案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其主要特征为,行贿人的目的是通过各种行贿行为成功承揽项目或签订合同。例如表格1中本不具备承揽项目资格的行贿人通过行贿承揽了项目,表格12中行贿人未经过招拍挂直接协议获得土地,并在其上开发房产项目,表格14、15、17中行贿人在招标中获得不正当帮助而中标项目,以及其他通过行贿取得项目或签订合同的情形。在此种类型的案件中,法院在划定违法所得的范围时,会将行贿人通过不正当方式承揽的项目或签订的合同所获得的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后认定违法所得。由于此类案件涉案金额较大,区分核算项目成本较为复杂,办案机关通常应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单位出具鉴定意见。
“差价型”案件主要特征为,行贿人的目的是通过行贿行为直接获得财产性利益,或减免本应付出的财产性利益,笔者形象地将其概括为获得“差价”。例如表格3、18中行贿人套取本不具有获取资质的国家补贴,表格9、12中行贿人减免本应缴纳的出让金或滞纳金,行贿罪经典案例中行贿人在商业交易过程中通过行贿行为不正当地抬高价格获得收益。在此种类型的案件中,法院在划定违法所得的范围时较为简单,通常将“差价”——即行贿人获得的补贴金额,减免的应缴金额,不当抬升价格的收益等——直接划定为违法所得。
“资质型”案件主要特征为,行贿人的目的是通过行贿行为获得本不具有的资质,既包括行为人为他人获取资质并收取费用,也包括行贿人为自身获得资质后从事相关经营行为。例如表格10、11中行贿人利用受贿人的密钥为他人办理虚假业绩录入,表格13中行贿人为本不具备注册资格的公司办理注册,表格20中行贿人本不具备评估资格,但通行贿行为获取评估资质,开展评估业务。在此种类型的案件中,法院在划定违法所得的范围时,前者可以直接将行贿人为他人违规办理资质所获得的收益划定为违法所得。后者的情况相对较为复杂,理论上虽然行贿人从事相关经营行为的资质是通过行贿行为获得的,行为人依据该行贿行为获得的资质从事经营活动,由此而获得的收益与行贿行为存在客观关联,似乎均应当划定为违法所得。但是,“不因犯罪而获益”原则要求获益必须与犯罪行为存在因果性关联,这种因果性关联不仅要求获益在客观事实上与犯罪行为存在自然的、紧密的、具体的联系,而且在规范评价上要求经营资质、实际经营能力和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资金充分程度以及既往经营成果等等因素在获得项目中的贡献程度,而且还要考察违法获得的资质是否影响到项目成果的质量状况。综合这些因素,如果资质的获得在项目获得和获益上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在所有获益因素中贡献最大,是其能够获益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可以认定获益是违法所得。否则,不宜超出作为行贿行为对价的获得资质的射程来认定违法所得。况且实践中,行贿人往往同时开展多项业务,难以严格区分其合法收入与违法所得,此时确认违法所得应当极其慎重,必要时要通过严格的鉴定评估认定。
(三)监察机关对违法所得范围认定的态度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成为贿赂犯罪的调查机关,实务中在监察机关调查阶段往往会先行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因此监察机关对于违法所得范围的认定态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登载的《如何准确界定行贿违法所得》一文中,将违法所得界定为直接产生、获得的不正当财产和间接产生、获得的不正当财产,并明确了两种应当视为违法所得和追缴没收等值财物的规定:(1)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转变、转化后的财物应当视为违法所得;(2)来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财物收益,或者来自已经与违法所得相混合财物中违法所得相应部分的收益,应当视为违法所得;(3)有证据证明依法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减损或者与其他合法财物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依法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物。[3]
三、单位行贿案件追缴范围的实践建议
综合上述理论和判例观点,我们可以对单位行贿案件违法所得追缴的实践应用得出一些建议。同时,行贿案件中违法所得追缴问题具有特殊性。其一,与一般犯罪违法所得相比,行贿罪的违法所得通常不体现为直接的财产性利益。其二,行贿罪的行为人实施贿赂行为通常就是为了进一步获得投资收益。对此,应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行贿罪的特点在实践中判断行贿罪违法所得的追缴范围。
1. 应当严格区分行贿案件中的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混合款项中违法所得的明确部分时,不应全部或部分追缴该款项
根据《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不正当利益”既包括结果意义上的不正当,也包括手段意义上的不正当,对于这两类不正当利益,均应当予以追缴。若行为人主观目的是为了获取正当利益,或自认为是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客观上获取的是正当利益的,当事人不构成行贿罪,相应的利益也不应被追缴。例如,甲具有申请补贴的资格,希望获得补贴而给予经办人员财物,经办人员按照程序向甲发放补贴的,甲客观上并未获得不正当利益,不构成行贿罪,所得利益不应被追缴。
在实践中违法所得范围划定的疑难案件中,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既有违法所得,也有合法所得的混合款项中与行贿行为存在明确对应关系的违法所得的范围的情况下,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审判机关不应判决全部或部分追缴混合款项。(相关判决可参见王东武、大连保税区鸿源化工有限公司单位行贿二审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9刑终45号)
2. 确定间接违法所得应当进行充分的因果性关联论证,辩护人可以围绕因果性关联展开辩护,维护当事人合法财产利益
不正当财产性利益既包括直接利益也包括间接利益。行贿罪的行为人实施贿赂行为往往是为了获得合法经营的机会,因此很难肯定其经营所得的合法性因素占主导成分。同时,在对违法所得进行追缴时,直接财产性利益的金额较易确定,间接财产性利益不易计算,例如,甲通过行贿行为获得了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优势,后通过正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财产性利益,又将收入用于投资、办厂、理财、置业等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属于间接财产性收益。基于行贿罪背后我国“零容忍”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司法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倾向于将行贿行为取得的不正当利益进行全面、彻底的消除。但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在认定间接违法所得时应当进行充分的因果性关联论证,排除与行贿行为不具有因果关联性的获益并扣除合理成本后来认定涉案违法所得。辩护人在进行辩护时,同样可以围绕当事人获益的因果关联性——尤其是司法鉴定意见的有效性——展开。当发现鉴定意见存在问题时,及时在给定期限内申请重新鉴定(逾期可能导致法院直接驳回相关辩护意见,参见陈某某单位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 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 [2018]湘0281刑初322号),避免当事人的合法财产被不当追缴。
注释:
[1]庄绪龙:《“犯罪所得投资收益”追缴的影响因素与判断规则》,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
[2]左袖阳:《违法所得投资收益的追缴:判断标准与追缴范围》,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
[3]温益华:《如何准确界定行贿违法所得》,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201/t20220119_165441.html,2023年3月1日访问。
作者简介
周金才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合规业务中心总监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同时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商事犯罪中心副主任。
周金才律师自1991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在三十余年的执业生涯中,承办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逾千起各类案件,尤其擅长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辩护、刑民交叉、刑事控告、刑事合规业务。周金才律师承办案件过程中,提出和践行“立体辩护”思路,众多案件取得了全案无罪、部分无罪、免予刑事处罚、实报实销、不起诉、终止侦查、变更强制措施等良好结果,以专业、敬业赢得了当事人及家属的认可,其中,部分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被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地方电视台及《法治日报》、《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转载。
周金才律师承办的部分案件中,有河南省万客来有限公司董事长侯某某非法占用耕地、虚报注册资本、合同诈骗案(得到最高层领导关注,经三次辩护最终三罪皆无);山东省德州市某公司董事长满某某先后被控合同诈骗、诈骗、骗取贷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历经四次辩护,全案无罪,获评2019年度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山东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刘某某巨额骗取贷款、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持有弹药案(部分无罪);全国劳动模范、辽宁省某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某某骗取贷款案(实报实销);中共河北省某市委书记系列巨额受贿案中张某某受贿案(公诉机关建议量刑14年,一审大幅度减轻处罚为9年);北方某省牛某某等20人被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第一被告人辩护,全案脱“黑”,部分罪名无罪);内蒙古自治区秦某某等12人被控恶势力案(为第一被告人辩护,二审开庭并全案改判);北京某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吴某某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集资诈骗无罪,总刑期由原判16年减为7年);北京某进出口公司股东张某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案(当事人审前被取保候审,一审免予刑事处罚)。
手机:13501101846
邮箱:zhoujincai@deheheng.com